39期[工作坊演講紀要] 許成鋼談「當代中國的探索歷程」
39期[工作坊演講紀要] 許成鋼談「當代中國的探索歷程」
演講日期:2023年12月7日
發佈日期:2025年12月11日
主講人:許成鋼(美國史丹佛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)
撰稿人:王致凱(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)
編按:2023年3月15日,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邀請許成鋼教授線上演講。講題為「中國極權主義的制度基因」,由本中心執委、合聘教授林宗弘老師與談(演講紀要可參見本通訊第35期,頁104-107)。同年12月,許成鋼教授訪台,在清華大學台北政經學院擔任客座教授。2024年起,每年秋季為研究生授課,並在台灣各學術機構演講,深入論述「制度基因」觀點。2024年11月,專著《制度基因: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》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。銷售量和討論度都很高,成為台灣學術界及出版界一大盛事。
而2023年,我們也已留意到,「制度基因」作為體系宏大、豐富的分析架構,許成鋼教授個人的經歷、思維及方法,自然值得關注。從而鎖定2021年出版的文集《探索的歷程》,於2023年12月7日邀請許成鋼教授蒞臨清華大學社會所,親自闡述學術思維及方法。演講至尾聲,「制度基因」架構呼之欲出。由於內容精深,紀要不易充分展現精彩完整原意,但期盼引起好奇興趣,一窺社會科學思維方法之堂奧,也增進閱讀理解許成鋼著作的知識基礎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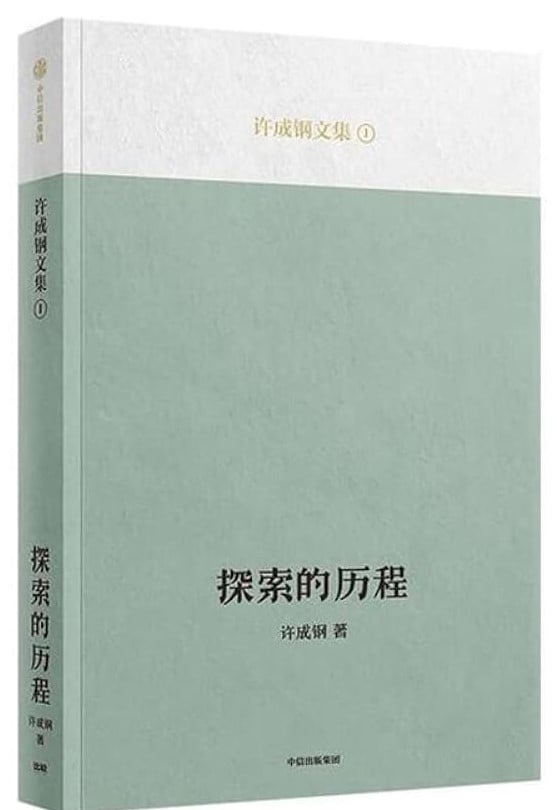
什麼是理論?什麼是科學?以物理學為起點
許成鋼的父親許良英先生,是近代中國知名的物理學家、科學史學家。由於家庭背景的緣故,許成鋼在早年自學經驗中,即對物理學、物理史跟科學哲學有所著墨。他自述對於方法論的見解,最關鍵的起點,是早年曾花大量時間學習物理學,這也開啟了他日後以物理學的方法去思考經濟學,並體察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異同之處。
其中,許成鋼自認「牛頓與愛因斯坦」是對自己影響最大的兩位物理學家。對他而言,愛因斯坦雖然顛覆了牛頓,但從方法論來講,愛因斯坦的工作性質其實是重複了牛頓的研究方法。許成鋼解釋:從馬克士威(James Clerk Maxwell)發展出的方程組(Maxwell's equations)統一了電學與磁學理論,並預測了電磁波的存在以後,愛因斯坦首先即看到,馬克士威方程組存在違反了牛頓物理學的部分。但與當時物理學家不同的是,愛因斯坦為了尋求解釋,他非常認真的去閱讀牛頓的原著。除了去釐清牛頓原著以外,也去看牛頓是怎麼構建這個理論,以及目前理論又遇到了哪些問題。愛因斯坦因此以相似方式,從這些破口中去另起爐灶,並發展出狹義及廣義相對論。
在這段物理史的回顧中,許成鋼提示了我們兩個重要的問題:「什麼是理論?」以及「什麼是科學?」。
「什麼是理論?」對於許成鋼而言,他受到物理學家恩斯特馬赫(Ernst Mach)的影響,這位同樣對愛因斯坦產生巨大影響的物理學家認為,理論就是「最經濟的思維」。許成鋼指出,經驗現象永遠是複雜而且看起來毫不相干的,人們之所以要找到理論,就是要用最少的假設,用邏輯的方法,把一大堆不相干的現象合在一起,以尋求統一的解釋,這叫做理論。而他認為,越是好的理論,越是統一的。許成鋼說明,這是他在去國外讀書之前,就深深根植在腦子裡的思維。而他所想像的社會科學,哪怕做不到,在想像中也應該朝這個方向去做。
而針對「什麼是科學?」許成鋼強調:科學的起點是「實證的觀察」,而科學的終點是「實證的檢驗」。他認為,科學面對的永遠是「現象」,沒有實證就不是科學。他進一步指出,這也是為何,當人們提到科學時,多數是從伽利略開始去談,而不是從古希臘時期。古希臘人雖然進行了對於外在世界的探索,但他們所使用的思維畢竟不是以「實證觀察」作為起點。許成鋼認為,只有有意識地「以實證的觀察作為起點,並以檢驗作為終點」,這才是科學。另一方面,許成鋼也強調,很多人會將數學與科學混為一談,但數學並不是科學。他說明,數學是人造的邏輯世界,因此可以任意作假設,只要推出來的結果符合邏輯,那就是數學的結果,並不需要去實證。但科學所推出來的東西,不見得就是結果,必定要回到經驗現象中去檢驗。
回到剛剛所提到的物理史,許成鋼強調,這就是馬克士威的貢獻。很多科學家在他之前,已經零星了解到很多「電」和「磁」的現象,而馬克士威則經由這些實證的觀察作為起點,去發展了出馬克士威方程組,然後預測了電磁波的存在,這也為後來赫茲驗證並觀察到電磁波鋪下了起點。
總而言之,數學不是科學,而科學需要數學,但卻也並不總是需要。比如生命科學絕大多數的工作,是透過大量的觀察,而社會科學也是如此。但許成鋼也強調,人的推理能力總是有限的,有些時候的確用自然語言就能進行推理,但當現象過於複雜時,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,數學能夠幫助科學家推理,的確是很重要的工具。
從機制設計理論談方法論
許成鋼指出,經濟學從亞當斯密開始,就有意地在模仿物理學的方法。當時雖然他們還不知道如何用數學構建其內容,但到十九世紀以後,經濟學家已經能部分地將經濟學的概念抽象化為數學。到了二十世紀時,朝這個方向的發展非常快速。一直到七、八零年代,這個「用數學去發展經濟學理論」的工作走到頂峰,之後就開始走下坡。從許成鋼的看法,他認為在這段時期,很多的經濟學家一些基本的問題上,混淆了數學與科學的分別。這個時期有非常大量的經濟學理論貢獻,然而,經濟學家只在數學式上說明了這個結果,並未驗證這些推論。回到剛剛所提的,科學的起點是「實證的觀察」,而科學的終點是「實證的檢驗」。這件事情在物理學上,我們只會說他「有待驗證」,而不會說那是物理的結果。這使得經濟科學一度產生了「偏離經驗現象」的偏差。
在七、八零年代,這套方法大為發展的時候,也正是「賽局理論」(Game theory;博弈論)發展的時候。當時普遍認為,一流的經濟學家都是在做賽局理論。包括許成鋼自身其中一個專業,即是作為賽局理論分支的「機制設計理論」(mechanism design)。機制設計理論最一開始,是來自於三、四零年代時,有關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」之間的大辯論。這場辯論先是由米塞斯(Ludwig von Mises)提出,他否定了社會主義實施的可行性,認為社會主義終究無法解決「資源配置無效率」的致命問題。與此相對地,朗格(Oskar Ryszard Lange)則持相反立場,並從嚴格的數學模型說明了,只要能達到市場均衡,必定能達成「柏拉圖最適」(Pareto optimality),並且兩者在數學上是「若且唯若」的關係。許成鋼說明,許多人看到這個式子,會以為朗格是在擁護資本主義。但恰好相反,朗格認為所謂的市場與所有制沒有關係,在他的模型中,只要企業能在市場上運作,就能達成柏拉圖最適。換言之,企業究竟是國有或者私有,並不會對市場運作的效率產生任何影響。進一步來說,朗格認為,在「沒有市場失靈」的前提下,「市場社會主義」(Market socialism)與資本主義是沒有差異的。而當人們進一步考慮市場失靈時,按照朗格的思路,市場社會主義則是更優於資本主義的制度。這套理論也成為了經濟學的基本教科書內容。然而,許成鋼指出,當這套理論成為教科書內容以後,多數經濟學家從未去看過朗格的原典,甚至不知其名,從而忽略了這套理論實際所關心的課題。許多人會以為,有關一般均衡理論的工作是在阿羅(Kenneth Arrow)及德布鲁(Gerard Debreu)的工作下完成的,但其實這兩位諾獎得主是延續了朗格的工作,以阿羅-德布魯模型(Arrow-Debreu Model)闡釋了現代意義的「一般均衡理論」(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)。事實上,即是將朗格的數學模型拓展到更多的情況。
許成鋼也說明,針對朗格的理論模型,海耶克(Friedrich Hayek)指出其忽略了兩個問題。用今天的話來說,這兩個問題叫做「信息不對稱」以及「激勵機制問題」。海耶克認為,朗格的數學模型將市場中的人過度抽象化,從而忽略了人和人之間所擁有的信息在現實中是不對等的。在資本主義市場上,信息問題之所以有機會被解決,是因為人們關心自己的利益,因此每個個人實際上是經由大量的努力去觀察,並獲得足夠的信息,從而做出對自身最有利的決策。但相對地,在市場社會主義中,制度設計者並沒有足夠的訊息去設計好的制度。另一方面,也因為產權是公有的,制度設計者缺乏足夠的動力去搜尋信息。簡言之,海耶克的批評主要建立於,朗格將個人因私有制而產生的自利動機,以及隨之而來的信息搜尋努力給「抽象化」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在這場辯論中,赫維克茲(Leonid Hurwicz)因緣際會地在英國、歐陸及美國,先後成為海耶克、米塞斯及朗格三人的學生。許成鋼指出,赫維克茲畢生的工作,即是試著透過「激勵機制的設計」來解決海耶克所提出的問題,也因此開創了「機制設計理論」。其中,赫維克茲的最大貢獻,是在和艾瑞克·馬斯金(Eric Maskin)、羅傑·梅爾森(Roger Myerson)的合作中,將賽局理論引入機制設計理論。他們認為,人們不見得需要一個制度設計者去制定一個計畫,而是需要設計一個滿足「激勵相容性」(incentive compatibility)的機制,去引導裡面的人依照他們的利益去行動。許成鋼即是馬斯金的學生。
赫維克茲在2007年獲得諾貝爾獎九個月後離世。許成鋼指出,在赫維克茲所發表的獲獎感言中可以發現,他本人非常清楚:實際上機制設計理論最後仍回到了海耶克對朗格的批評點上。也就是說,機制中的每個人事實上沒有理由去信任機制設計者的判斷,除非設計機制的人是全知全能,並且受人們信賴的上帝。總言之,在信息不對稱與激勵機制問題上,機制設計理論仍有其未能克服的課題。
在說明機制設計理論的發展後,許成鋼隨即向我們提點了方法論的重要面向。他指出,如果經濟學是社會科學,而社會科學對任何理論的判定是「經驗判定」,而不是「理論證明」的話。其實從經驗上,無論是從東歐或者是中國早期改革開放的經驗中,都已經說明了「信息不對稱」與「激勵機制不足」的前提下,社會主義國家必定會出現「軟預算約束」(soft budget constraints)的問題,從而導致市場社會主義成為行不通的體制。但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說,七零到八零年代以前的經濟學,過於強調數學推理而忽略實證,大量學者將數學與科學混淆,而使得經濟學多走了不少彎路,最終於八零年代進入死胡同。然而,許成鋼更指出,在八零年代以後,經濟學雖然開始進行實證面的翻轉,但卻又忽略了經濟學的理論。他認為,當代的經濟學已經不再做重大問題的理論驗證與推測,而是從統計學的作法來進行推論。許成鋼強調,統計學是數學,而數學不是科學。經濟學現在多數的實證工作,又落入了統計學的陷阱之中,難以稱之為科學。
社會科學理論的統一性
演講中,社會所陶逸駿老師向許成鋼老師提出了幾個問題,除了涉及新制度經濟學,以及經濟學與其他學科間的關係以外,更觸及社會科學的諸多基本問題。
陶逸駿的第一個問題是:「赫維克茲最後所觸及到的上帝視角問題,是否使經濟學的研究引導到權力分配的問題,甚至可能與當代的政治學理論有所連結。」對此許成鋼指出,就學界的運作情況來看,經濟學從八零年代以後,已經出現了大翻轉。以至於當代年輕的經濟學家幾乎已經不看理論,甚至不知道這些曾經的辯論及其背後的重要課題。而作為主流的計量經濟學,實際上就是統計學。再者2007年以降,機制設計理論能雖然有好幾群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者,但其理由已經不是因爲上述辯論與重大課題,而是因這個理論後來發展得相當複雜並且實用,並解決了大量的實務問題,使得有一些人開始認為經濟學已經開始走向類似「工程學」的方向。例如拍賣、腎臟移植的問題,都是透過機制設計理論去解決的。但即使如此,目前的經濟學界並沒有持續去試著解決剛剛所提到的、「信息不對稱」與「激勵機制」這些背後最大的問題。但許成鋼也認為,這個問題的確超出了經濟學的問題。這不僅涉及政治,事實上,選擇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,也從來就不只是單純的經濟問題,甚至從來都與政治有關係。但當我們將經濟學理解成只處理資源分配的學科時,實際上,的確會縮窄成技術問題。
陶逸駿的第二個問題是:「寇斯(Ronald H. Coase)的觀點跟這場辯論是否有內在關聯?」寇斯理論認為,只要產權的配置是清晰的,而交易成本為零,則產權初始的配置並不影響經濟效率。許成鋼說明,這個理論經常被詮釋成:只要當初的產權清楚,那麼所有權並不重要。以張五常為例,他認為中國在土地上實行全面國有制是無所謂的,因爲產權是清楚的,所以人們只要關注交易成本為零即可。許成鋼進一步指出,事實上所謂的寇斯理論,就是一般均衡理論的一個特殊情況,只不過一般均衡理論沒有考慮到產權,而寇斯則告訴我們:在哪些情況下,我們可以不關心產權。但許成鋼點出,真正的問題在於:「什麼是交易成本?」他說明,尤其當我們討論到討價還價所牽涉的成本時,這就牽涉到,「這是不是法治社會?人們為什麼能討價還價?人的地位是不同時,一個人怎麼能討價還價?在中國,一個私有企業老闆能跟黨幹部討價還價嗎?」許成鋼認為,寇斯理論雖然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,但並沒有將問題解釋清楚,等於將重要的內容關進了「交易成本」這個黑箱子裡頭。新制度經濟學的另一位巨擘,諾思(Douglass C. North)則引入交易成本概念,並提出相關路徑依賴(Path Dependence)理論,以說明制度的演變及其依賴性。但許成鋼說明,當我們非常認真去看待路徑依賴理論時,我們其實難以說明其原因。雖然諾思對此的解釋是,「規模報酬遞增」(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)使得原制度在路徑演變時發揮了效果。但許成鋼認為,實際上有大量的制度問題,尤其當其牽涉到經濟以外的問題時,並無法透過「規模報酬遞增」的理由進行說明,以至於其解釋力相當侷限。許成鋼進一步分享,這也是為何,他這幾年將制度依賴視為一個黑盒子,並試著去將其打開,而提出「制度基因」(Institutional Genes),以作為路徑依賴的解釋。他認為,在給定的制度環境下,人們出於自己利益的考量,有意地去選用並避免拋棄跟自己利益相關的部分,以至於原有制度的成分被延續,從而形成了制度依賴。
陶老師的第三個問題是:「當學者在處理社會科學解釋上的『統一性』時,同時又要面對越來越複雜的實際現象。以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為例,諾思到了晚年開始更關注意識形態的課題,從而與主流經濟學越來越遠,納入了更多學科的觀點。許成鋼老師是如何看待這兩者之間的張力?」許成鋼指出,這個問題實際上牽涉到了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,亦即:社會科學是不是科學?許成鋼認為社會科學不僅僅是科學,甚至與自然科學並沒有太大的差異。他認為,當代反對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畫上等號的理由,大概有以下幾種:第一個理由是,自然科學所面對的現象,比社會科學所面對的世事變化來得簡單。但許成鋼認為,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,現在人們已經知道,自然環境也存在著高度複雜的現象,例如地震、生物進化,這些複雜的系統並不比社會科學所面對的現象來得單純。第二個理由是,自然科學研究的是人之外的對象,是一個封閉系統,而人類難以干預,但社會科學的研究是其自身,因此研究者可能干預其自身。但許成鋼認為,這樣的分野也並不清晰存在。以量子力學為例,測不準原理已經告訴我們:只要研究者進行觀察,他就已經進行了干預,從而粒子的位置與動量是無法被同時被確定的。許成鋼說明,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,現在人類已經知道,自然科學所從事的工作,也是在開放系統下進行測量與觀察。第三個理由是,自然科學可以做實驗,而社會科學不能做實驗。然而,當代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社會科學家開始進行實驗。固然,許成鋼對於社會科學所進行的實驗有諸多批評,但並不認為這能作為區分自然與社會科學的理由。他認為,自然科學中的確有大量內容是依賴實證,但「實證觀察」從來不能與「實驗」劃上等號。例如,宇宙學的重大發展就是依賴觀察,而不是實驗。而研究長期氣候變化的科學家,他們也不能作實驗。他想說的是,人們並不應該將實證觀察與實驗混為一談。許成鋼分享,過去他也相信這三個理由,但現在的他並不認為這三個理由能合理地為「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存在明確分野」的命題進行支撐。
在此基礎下,許成鋼進一步進行回應:如果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不存在明顯界線的話,那我們要如何去發展社會科學?受到馬赫的影響,他強調科學一定要有「理論」,而理論是「經濟的思維」。而所謂「經濟的思維」,就是「用最少的假設對經驗現象提出最多的解釋」。但在當代,無論是經濟學、政治學、社會學,或者人類學家,社會科學家大多都並未按照這樣的思維去發展理論。他認為之所以如此,是因為社會科學各個領域都不太關心科學哲學的問題,而科學哲學卻又是指導科學發展的重要思考。至少在物理學上,一些重要的科學哲學家都經常是物理學家。許成鋼認為,如果什麼東西都有一個理論,那他就不是理論,而更接近對於實證的紀錄。他強調,對於實證的紀錄並非沒有價值,但絕難稱之為「理論」。
以自然科學的發展為對照,許成鋼指出,牛頓至少是站在兩個巨人的肩膀上發展理論。一個是伽利略,提出了自由落體的公式;另一個則是克卜勒,在經由大量觀察後,提出了行星運作的橢圓方程式。即使如此,並不是有公式就有理論,他們並沒有提出讓人信服的道理,只是單純對經驗現象進行描述。而牛頓的工作,就是在他們的基礎上去尋找道理,這才叫作理論。當代的經濟學就是做了很多伽利略、克卜勒、安培、伏特等人的工作,但沒有人做牛頓跟愛因斯坦的工作。許成鋼的意思是,沒有人把大量的實證觀察去串在一起,去創造一個理論。許成鋼也感嘆,他認為當代的社會科學家並不在乎這個問題,但他個人認為,社會科學如果要發展,必須要發展一個統一的理論。但他也提醒,這是他個人的觀念,是哲學觀,而哲學不是科學,聽眾們可以選擇要不要接受。
對於中國政治經濟的預測
隨後,社會所姚人多老師也進行提問,許成鋼老師也因此對中國經濟預測的基本思路進行了分享。
姚人多提問:「您在報章媒體上,對中國的經濟情況的預測相當悲觀。這是您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本身抱持悲觀,還是是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感到悲觀?」對此許成鋼認為,每次當其他人說自己悲觀時,他都會強調自己是「客觀」。許成鋼強調,他所做出的任何預測,從來都不是基於任何意識形態,或者基於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程度所提出的觀點。他點出,他一直在強調社會科學的理論,實際上,他的這些判斷都是在「給定現在的情況下」,從理論根據及其後面的機制,所作出的判斷。實際上,許成鋼認為自己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大趨勢通常是對的。但十幾年前的時候,同行裡面很少有人同意他的判斷。原因也很簡單,因為人們所認識的機制是不同的,大家用不同的機制去看現在的情況,所得出的結論自然也是不同的。
陶逸駿老師進一步追問:「當時情況背後的機制是什麼?」許成鋼指出,首先要看私營企業是如何運作,其次就是看國有企業的運作。從理論上來講,國有企業會面臨軟預算約束,而從經驗上看,「國進民退」的確一直在進行,而這後面會衍生出大量的債,這些都是清楚運行的機制。陶逸駿老師再問道:「從您的新書中,您觀察到的『制度基因」,尤其是改革開放一些制度特點,像是分權,在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的時期就已經有了。而諾斯在提路經依賴時,他個人會關注制度上的秩序跟創新。如果要用制度基因的概念進行分析,改革開放後,有哪些是既有的,又有哪些是創新的?」許成鋼回應,從他的角度看,他會選擇不關注這個問題。從他的方法論來說,他認為有意識地去作區分,反而會把很多該簡化的概念變複雜,反而不利於理論的簡化工作。而許成鋼認為,從文化大革命到改革開放,基本來看,其實沒有什麼制度是真正「創新」的。真正該回答的是,中國的改革經驗跟蘇俄、東歐都非常不一樣,沒有必要討論這是不是制度創新,但為什麼他們不一樣,以及到底能走多遠,這才是該被回答的。許成鋼認為,從理論上來看,「分權式極權制」比起「集權」會更能帶來激勵機制,但說到底,它畢竟是極權制度。政權的生命雖因分權而延續,但這個制度的基本特點,並不會把它變成一個「不是極權」的制度。
